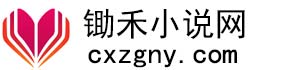100-104(19/19)
里,在那样荒唐而无路可退的方式里,把所有都说了。可她现在再也没力气否认了。
他已经死了。她一再躲避,如今也没有了再逃避的理由。
外头的天色亮了一线,白得像旧宣纸上褪了墨,只剩一摊苍白。
钟薏坐起身,披衣下榻,冷意扑上来,她忍着没缩。
今天还有许多事要做。
她做惯了这些,父亲的年年要烧。花匠他们的她也烧,可自己从没想过,有一日会为他也烧上一份。
这样想着,钟薏收拾好,披上斗篷,去街上挑了几束香,一大叠冥纸,又折去另一家铺子买了黄裱纸。
若是不全给他捎过去,怕是今夜又要来缠着她。
纸张薄而脆,她将几样东西一一收进怀里,想起今日要来的富商,算着时辰匆匆折回小药坊。
巷子清冷,风擦着脸颊吹过,难得有些干冷。
刚走到门口,她却骤然顿住脚步。
有什么重重撞上胸口。
心跳、耳鸣,还有“砰”一声。她手一松,怀里香纸跌落一地。
香烛碎裂,冥纸飞散,轻飘飘地顺着风在脚边翻了几圈,裹着纸屑卷进门内。
落到房内人的脚边。